古籍名著《切韵》的年代、作者和内容精讲
互联网
作者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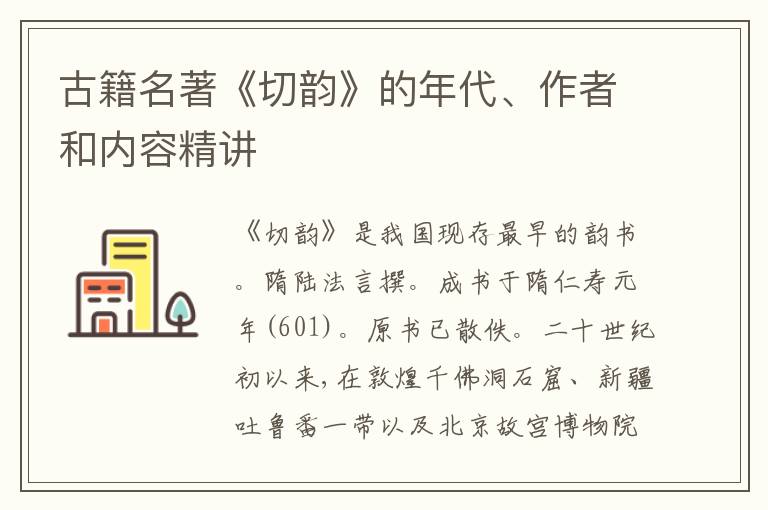
陆法言(生卒年不详),名词,又名慈,以字行。隋魏郡临漳(今属河北省)人,音韵学家。祖先是鲜卑人步陆孤氏,魏孝文帝迁都洛阳,步陆孤氏汉化而改姓“陆”。其父陆爽在隋文帝时官太子洗马。陆法言敏学有家风,官承奉郎。开皇二十年(600)因其父替废太子勇之子改名事,被屏黜。
据 切韵序,隋开皇九年(589)某日,有刘臻、颜之推、卢思道、李若、萧该、辛德原、薛道衡和魏彦渊八人,同诣陆法言家中,聚会饮宴,并论及音韵之事。以为 “古今声调,既自有别”,诸家韵书的取舍,亦复不同,于是众人评论“南北是非,古今通塞”,“捃选精切,除削疏缓”,而由陆法言 “烛下握笔,略记纲记”。十一年以后,法言罢官,屏居山野,交游阻绝,“遂取诸家音韵,古今字书,以前所记音,定之为 切韵五卷”。
切韵共五卷,平声字多,占一、二两卷,上、去、入声各一卷。切韵的收字,据封演 闻见记,“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”;而式古堂书画汇考载孙愐 唐韵序云: “今加三千五百字,通旧为一万五千字”,唐韵是就 切韵加字编成的,则 切韵原本收字当为11500字,与封演所记不同。本书分韵193韵,其中平声54韵,上声51韵,去声56韵,入声32韵。
根据唐人抄本 切韵残页、唐人增订本 切韵和其他文献资料,可知陆法言切韵的体例有以下特点:1.平声54韵序号一连到底,不象广韵那样上、下分断。2. 广韵的真与谆、寒与桓、歌与戈合为一韵。3. 覃、谈二韵在歌、麻二韵之后,蒸、登二韵在盐、添二韵之后,去声霁、祭、泰、卦的次序作泰、霁 、祭、卦;入声次序也和 广韵不同。4. 书首列韵目表,每一韵目前,大多有一个数字标明韵目次第。5.多韵之中的字按同音关系分成不同的小韵,各小韵首字下先出训释,后注反切,再出字数。6. 韵字的注释十分简单,有的根本没有注释;注释一般不注出处。7.不正字形。
陆法言切韵序云: “欲广文路,自可清浊皆通;若赏知音,即须轻重有异。”文路是指创作诗文的用韵,知音是指语音方面的审音和正音,所谓 “切韵”,正是指切正语音。又对于切韵一书“多所决定”的颜之推曾批评“阳休之造切韵,殊为疏野”,“王侯外戚,语多不正”。( 颜氏家训·音辞篇) 由此可知,切韵一书的编撰目的,一方面是为诗文创作中的选韵检字之用,另一方面又是为语音的辨正和研究之用。由于这两个目的,所以陆氏等人把当时的读书音作为标准音,依照标准音来评判各家韵书,依照标准音来进行分韵。这样,凡是主元音和韵尾不同的读音,必定分入不同的韵,而凡是主元音和韵尾相同的读音,不管韵头如何,也必定合并在一韵之中。因此切韵的分韵要比当时其他粗疏的韵书细密得多,其193韵实在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忠实描写。
切韵在汉语音韵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:1.切韵如实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,使后人能够据以考证出隋代和唐初的汉语语音系统,并以此为基础,上溯汉语上古音,下推汉语近代音。2.从切韵出发,可以说明现代汉语各方言的语音变迁和方言之间的语音关系。除闽方言部分语音现象外,几乎所有现代分歧巨大的方言,甚至包括日语吴音、汉音、高丽译音和汉越语这些域外方言,都可以合理而系统地从切韵推导出它们的演化轨迹。3. 利用切韵可以纠正广韵等韵书的讹误。如广韵梵韵“剑、欠、俺”三字反切下字与本韵其他字不相系联,陈澧切韵考以互见法并为一类,而在切韵中此三字并在去声严韵,可见此三字与梵韵本不同类,广韵误植。4.切韵影响了包括 唐韵、广韵、集韵、五音集韵和平水韵在内的一大批韵书,形成了整整一个系列的韵书,并在音韵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,被称为“正统韵书”。切韵的研究对于唐韵 以下诸韵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切韵虽是一部极有价值的韵书,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,主要是: 1. 分韵欠精密。如切韵无上声广韵、去声严韵,后由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补足。2. 收字归韵尚有错误。如“恭、蚣、枞”三字当属鍾韵,切韵误入冬韵。3. 训释和反切有误。如“蕃”为草盛,误训为蕃屏;“��”为火戈反,又希波反,切韵误漏反切。4. 许多韵字没有训释或训释过简。
历史上关于切韵性质的讨论,可以分为三个时期:1. 从唐代至清代乾嘉学派以前,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切韵是不是吴音的问题上。如唐李涪刊误以晚唐洛阳音与切韵音比较,认为陆法言所记为吴音,与中州音不合,而苏鹗苏氏演义则认为陆氏本鲜卑族子孙,非吴郡人,切韵所记为当时的正声雅音。2. 从清乾嘉学派开始到章炳麟、黄侃为止,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 切韵分韵的问题上,如戴震认为切韵是“有意求其密,用意太过,强生轻重”,陈澧则认为陆氏分韵,“非好为繁密也,当时之音,实有分别也”。3. 从高本汉以后至今,讨论内容主要是: (1)切韵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?切韵是不是一时一地方音的记录?(2)如果切韵是综合音系,那末它有没有基础音系?基础音系是什么?(3) 切韵与现代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?主要代表如高本汉、周法高认为切韵代表了隋唐时代的长安方音;王力认为切韵代表当时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,这个系统是参照古音和方音来规定的;罗常培认为切韵是各地方音的最小公倍数,只要当时或前代某地的语音有别,切韵就从分不从合;王显、邵荣芬认为切韵以洛阳音为基础方言,并吸收了金陵话的特点;周祖谟认为切韵具有严整的体系,音系基础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文学语言,即读书音系统。
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,切韵的研究受到了汉语音韵学界极大的重视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韵书、韵图和前人的研究成果,整理出切韵的音类系统,又参照现代汉语各地方音和中外译音,成功地构拟出切韵的音值,从而使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现在世人面前。以后许多卓越的中国学者,如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方桂、王力、陆志韦、董同和等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,对高说进行修订和补充。其中讨论最为集中的问题是:1. 喻化声母;2. 重纽;3. 介音;4. 重韵;5. 唇音字; 6. 元音的数量; 7. 纯四等韵有无i介音等。到目前为止,虽然学者们的许多分歧意见仍然存在,但是作为中古音代表的切韵的语音面貌已经基本搞清。普遍的认识是切韵有35个左右声母,110个左右韵母,4个声调,10个左右元音,2个介音,3个塞音韵尾,3个鼻音韵尾和2个元音韵尾等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