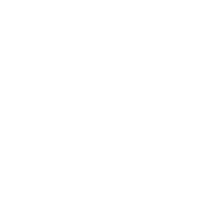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全文、翻译和鉴赏
互联网
作者:

(节选)
太史公曰: “先人有言①: 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②,有能绍明世③,正 易传,继春秋,本诗、书、礼、乐之际?’ 意在斯乎! 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④。”
上大夫壶遂曰⑤: “昔孔子何为而作 春秋哉?” 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⑥: 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⑦,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⑧,以为天下仪表: 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⑨。’ 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 夫春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⑩,故长于变; 礼经纪人伦(11),故长于行; 书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 诗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(12); 乐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 春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,乐以发和,书以道事,诗 以达意,易 以道化,春秋 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(13)。万物之散聚(14),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,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易曰: ‘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。’ 故曰: 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。’ 故有国者,不可以不知 春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,不可以不知春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(15)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(16)。为人君父,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,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为之,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(17)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 春秋 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(18)。”
壶遂曰: 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 春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(19)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。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 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 伏羲至纯厚(20),作易、八卦; 尧、舜之盛,尚书载之,礼乐作焉; 汤、武之隆,诗人歌之(21)。春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 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(22),获符瑞(23),建封禅(24),改正朔(25),易服色(26),受命于穆清(27)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(28),请来献见者,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,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(29)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春秋,谬矣!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(30),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(31)。乃喟然而叹曰: “是余之罪也夫! 是余之罪也夫! 身毁不用矣!” 退而深惟曰: “夫 诗、书 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(32); 孔子厄陈、蔡,作春秋(33); 屈原放逐,著离骚; 左丘失明,厥有 国语(34); 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(35); 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(36); 韩非囚秦,说难、孤愤(37); 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(38),自黄帝始。
【译文】 太史公说: “先人曾经说过: ‘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就有孔子。孔子死后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,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考定易传,续写春秋,探求诗、书、礼、乐之间的本原而做著述?’ 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? 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? 我怎敢推辞呢!”
上大夫壶遂问: “从前孔子为什么写 春秋 呢?” 太史公说: “我听董仲舒说: ‘周朝政治衰微,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,推行王道,诸侯忌恨他,大夫阻挠他。孔子知道他的话没人采纳,政治主张无法实现,因此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系列大事的得失,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: 讥评天子,斥责诸侯,声讨大夫,都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。孔子说: ‘我想与其把是非褒贬的事情寄托于空口说白话,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显著明白。’ 春秋 这部书,上则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,下则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,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,判明正确和错误,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,善者善之,恶者恶之,贤者贤之,不肖者贱之。已亡的国家把它恢复起来,已绝的世系把它延续起来,补救弊端,振兴已荒废的事业,这都是王道重要的内容啊! 易 谈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所以它最擅长于讲变化; 礼安排人们的等级关系,所以长于引导人们的行为; 尚书记录先王的史迹,所以长于政事; 诗 记载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所以长于讽喻; 乐 是礼乐建立的依据,所以长于陶冶性情; 春秋 明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,礼 用来节制百姓,乐 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,书用来指导政事,诗 用来表达思想,易 用来说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,春秋 用来阐明仁义,治理乱世,使之复正,再没有比 春秋更切近的了。春秋 的文字有几万,它的要旨有几千条,万事万物或散或聚,都总汇在春秋一书里面。春秋 一书之中,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,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,四处流亡、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诸侯更是多得不可胜数。考察它的原因,都是丢掉了王道这个根本啊。所以 易 说: 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 所以说: ‘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,它的起始和发展已经很久了。’ 一国的君主不可以不懂春秋,否则眼前有进谗言的人却看不见,身后有奸贼也不知道。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 春秋,否则处理日常事务,而不知道采用适宜的方法,遇到意外的变化而不知道临机应变。做人的君主、父亲,却不通晓春秋 的要义,必然蒙受罪魁祸首的名声; 做人的臣下、儿子,却不通晓春秋 的要义,必然陷入篡位弑君的极刑,得死罪的名声。其实他们本心都以为是件 ‘善’ 事才去做的,但由于不懂得春秋要义,以至于犯了错误,受到舆论谴责也不敢推辞。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,以至于做君的不像君,做臣的不像臣,做父的不像父,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这样,君不像君,就会被臣子侵犯; 臣不像臣,就会被诛杀; 父不像父,就没有道德规范; 儿子不像儿子,就会不孝。这四种行为,是天下最大的过失。把天下最大的过失给他们,只好接受而不敢推辞。所以 春秋是礼义的本原啊。由于礼教是防范于某些坏事未发生之前,法律是施行于某些坏事发生之后; 从而法律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被人看见,而礼教的防禁作用则较难被人理会。”
壶遂说: “孔子那个时候,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,下面没人任用他,所以他作了 春秋,留传下一些空口说白话的条文来裁断礼义,把它当成一种王法看待。今天你上面遇到圣明天子,下面得以保住您的太史令之职,万事都已具备,都各自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 您说的话,想用来说明什么道理呢?”
太史公说: “嗯,嗯,不,不,不是这样。我听先父说过: ‘伏羲氏时代最为纯真厚道,他作了 易、八卦; 尧、舜的盛世,尚书记载下来,礼、乐也兴起了; 商汤、周武王时代的兴隆,诗人歌咏赞颂。春秋褒扬好的,贬斥邪恶,推崇三代的道德,表扬周室,它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。汉朝兴起以来,直到当今圣明天子接位,得到上天的祥瑞,建坛祭神,使用新的历法,天子所使用的车马改用新的颜色,受命于上天,德泽流布,无所止极,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经过几重翻译,前来边境上叩关请见,请求贡献物品拜见君主的人数,多得不可胜数。臣下百官,竭力颂扬圣上的明德,仍然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。况且,士人贤能却不能被重用,这是做国君的耻辱; 皇上英明智慧而德行却没有被广泛传扬,这是官吏的过失啊。况且我曾任太史令,废弃英明智慧盛德不去记载,磨灭功臣、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不加表述,丢掉先父的遗教,罪过更大了。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,整理编次他们的世系传记,并不是什么创作。先生把它与 春秋 相比,完全错了。”
于是我就编写这些文章。写了七年后,我突然遭到了李陵之祸,被囚闭在监牢之中。于是喟然长叹,说: “这是我的罪过吗? 这是我的罪过吗? 我的身体遭到毁坏,再没什么用啦!” 平静下来深思道: “大凡诗、书 隐约其辞的地方,都是作者志虑深思的地方。从前西伯 (文王) 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,推演了 周易; 孔子被围困在陈、蔡的时候,后来作了 春秋; 屈原遭到放逐,赋了 离骚; 左丘失明,著了 国语; 孙膑受了截膝的刑法,就研究编辑兵法; 吕不韦迁到蜀地,世上流传他的 吕览;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,写下 说难、孤愤; 诗经 三百篇,大多是圣贤之人感情激发才创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志向被压抑,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,所以记述往事,想作为后世的借鉴。” 于是我就记述了陶唐以来的事情,上从黄帝开始,下到当今皇上猎获白麟的那一年为止。
【鉴赏】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自述家世生平及关于写作史记 的有关情况。他充满信心,要做孔子第二。孔子写过春秋,他也要写一部春秋第二的 史记。本文通过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,以评述孔子 春秋 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史记 的目的。孔子 “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: 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” 而作春秋,以 “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”; 司马迁身处汉初,“臣下百官,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”,加之他遭李陵之祸后,想到西伯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孙子、吕不韦、韩非等贤圣发愤之作,“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”,因而他作 史记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
本文的写作之妙及其作用,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一书中有过中肯的评价,他说: “盖自序非他,即史迁之作之列传也。无论一部史记,总括于此,即史迁一人本末,亦备见于此。其体例,则仿易之序卦传也,诗 之小序也,孔安国 尚书百篇序也,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。其文势,犹之海也,百川之汇,万派之归,胥于是乎在也。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 史记之法也。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,莫不于是灿然明白。未读史记之前,须将此篇熟读之; 既读史记之后,犹须以此篇精参之。文辞高古庄重,精理微旨,更奥衍宏深,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。” 总之,本文是引导我们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和 史记 的指路之作。